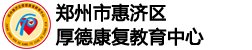战胜孤独症(待续)
战胜孤独症(待续)
[美]乔治安娜·托玛斯著
孙敦科泽
(接上期)
不能与人们交往还不是我的唯—问题,我还存在其他一些感觉方面的问题。例如,在上学的路上有一座旧的大楼,叫做圣·乔治旅馆。旅馆旁边的砖墙上有—个圆圆的小排水管,其直径和飞碟的直径差不多。排水管正面覆盖有金属的隔栅,砖墙表面使得排水管不引入注意,听不到污水的流淌。
我们每天上学路上都要走过那家旅馆,由于排水管发出非常微弱的噗噗声,吓得我六神无主,我都没法走在排水管那一边。我当时没认识到,除了我,准也没听到这声音。排水管发出有节奏的、噗噗响的噪声,听上去就像野兽在追赶猎物时所发出的粗重的喘息声。我无
法靠近它,不明白为什么排水管会发出那种噪声。那噗噗声有一种快速脉动的节奏,给我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排水管里有一个妖怪,妖怪呼吸时发出那种频率很低的、有节奏的声响。我无法辨认的各种声响总是令我害怕,但它听上去就像有一条龙在排水管里面喘息,这是我
所遇见过的最令我毛骨悚然的一样东西,而且竟然没人注意过它!
每当我走过圣·乔治旅馆那排水管时,我开始发出尖叫、大声喊叫,捂住我的耳朵去隔绝噗噗的声响。无论是走过,还是开车经过,—想到要路过那里,我怕得要死,没等到达我就开始尖叫起来。最后,我的父母有点明白了,就绕道走,绕过圣·乔治旅馆走。
我班上的其他孩子斜靠在排水管上,他们说排水管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心烦意乱。那时,消息传开,说我对排水管怕得要死,因为最后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母亲。没有一个孩子能理解我的恐惧,大家都认为没有道理,可它却成了我父母的一大“负担”[2],他们不得不一直绕道走。对我的父母来说,我的恐惧是一个谜。没人认识到,我是因为听觉过度敏锐才这样的。所有穿着校服的孩子靠在墙上、靠在发出噗噗声响的排水管上,根本没有害怕的迹象。当我看到,我的同学们并不害怕,我明白了,我与众不同,准是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甚至他们听不到的声音,我却怕得要死。
一年级刚开了头,马上就结束了。这是感觉方面的一场噩梦,它是噪声和过度刺激所造成的。由于感觉方面负担过重,我完全退缩了,不去理会其他的孩子,我不能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个交流。他们指派我去的班级吵闹得我无法忍受,他们要我和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在—起。我每天都是自我封闭、隔绝一切。在学校,我唯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洒满教室的自然光,有了它就不再需要日光灯了。
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我的老师或者其他的孩子,当时我与他们完全是隔绝的。我唯一记得的是教室的内部、那座大楼以及学校的操场,因为我不隔绝无生命的东西。我只隔绝产生噪声的东西,而人则是吵吵闹闹的。我对大楼和环境的回忆要清楚得多,因为我不曾像隔绝人们那样去隔绝它们。我从任何会引起我感觉负担过重的东西那里退缩,而大楼不会,大楼是静悄悄的。人们是吵吵闹闹的,而且无法预料;大楼却总在那里。结果,大多数把我作为孩子来交流的人们,在我的记忆中被隔绝掉了。我根本记不起来他们,但我仍能记起我上学时走进过的、或者生活过的每一座大楼,连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都记得。
重返勒福医疗中心
开学之后没过几周,我又回到了——勒福医疗中心。上正常学校的实验,由于我感觉负担过重和自我隔绝,可悲地失败了。公立学校的气氛令我受刺激过度,因而我的孤独症症状看上去更加严重了。我唯—的选择是返回勒福医疗中心,我的母亲懊恼极了,因为她曾希望
我能随班就读,可这希望已被打得粉碎。
一年级余下的时间,我报名在——勒福医疗中心门诊。这样我住在家里,只是白天去——勒福医疗中心上课和治疗。那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因为他们把我放回到原来的孤独症部,和原来的那些孩子在一起。孤独症部里还有一些原来的辅导员、护士和医生。至少这里环境熟悉,也安静得多。
返回勒福医疗中心之后,最为糟糕的是经常要做血液检验。每个星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摇摇摆摆走进门来,带我再一次去做血液检验。我就知道,又该轮到我去遭罪了。我没法抵制那些医生,不管我多么紧张、多么恼怒、多么无助,他们还是要带我去的。我觉得就像被带到刑训室去—样。
我从来也没习惯过这种缓慢而痛苦的折磨:把针头插进我的血管,直到血液灌满注射器。我的过度敏感的触觉使这种血液检验更加痛苦,而我又无法避免血液检验。我以为他们是在检验我有没有白血病,因为我姐姐曾经得过。我产生了一种极度恐惧,怕会流血致死,怕我会死去。我见过我姐姐由于输血和化疗,身上插满了管子;所以我以为要我验血一定与她那种疾病有关,这使我精神上受到创伤。
我还记得曾经在——勒福医疗中心看见过—个大实验室,那里储藏有数以千计的玻璃管,有人曾经领我看过他们保存血液和其他物质的玻璃管。由于患有孤独症,我从来没想到要去告诉父母我在接受定期血液检验这件事。我原以为这—切很正常,因为我见过我姐姐住院时就经历过输血。我想验血是我住院计划的组成部分,我没有别的选择。
在——勒福医疗中心,学习计划是强化的,需要集中注意力。我的—个教室在底层,没有窗户, 我记得的是:被灯光照得亮堂堂的教室、一块黑板、刷得雪白的墙,还有蟑螂。我在——勒福医疗中心学习经历中仍然记得的一件大事,我曾站在黑板上踩死了一只很大的蟑螂。我脚底下啪的一声,声音很响亮。我抬起脚一看,踩碎了的蟑螂冒出了白浆,令我神往。我喜欢踩蟑螂,因为脚下嘎吱一声的那种感觉,就像吃苞米花—样。离开——勒福医疗中心以后,我不再这样做了。那里的教学活动包括用色彩鲜艳的毡制字母来学习拼音字母,这些字母摸上去很柔软,可以像尼龙裕裢—样把它们粘到毡制的黑板上。我喜欢摆弄这些毡制的字母块,我把它们粘到黑板上去,柔软又悄无声息,而且色彩鲜艳。同样我还摆弄数字块,数字块的颜色也非常醒目。这种学习方法非常有效,因为我是一个对颜色敏感的、凭借视力的学习者。——勒福医疗中心的老师们懂得运用颜色和质感来教我字母和基础算术,在这—点上,他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我的其他教室在顶层,隔壁是围有篱笆的屋顶游乐场。每次到外面去玩,其他孩子在做游戏,我却在收集鸽子羽毛。我喜欢羽毛的质感,我会一连几个小时玩羽毛,让手指滑过羽毛。我对鸟类完全入了迷,我有—个小小的存放羽毛的壁橱,一个学年下来,我攒了好多好
多羽毛。大楼房檐上有数以百计的鸽子在那里筑巢,我常常侵犯它们的栖息地。我喜欢鸽子,喜欢鸽子的羽毛,喜欢它们安安静静,不会引起我感觉方面的问题。我的
我在——勒福医疗中心的第二年充满了音乐,我学会了像《玛丽·马克小姐》、《耶利米原来是一只牛蛙》这样一些歌曲。每天当我和我母亲穿过布鲁克林桥,在行驶到—勒福医疗中心去的路上,我们听着《摇摆的知更鸟》。许多歌曲我都是在收音机上学的。那一年我还学会了一些圣诞颂歌,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叫《小鼓手》,因为歌声随着鼓点是那么的轻柔。
我参与了我并不喜欢的社交性的互动活动,因为太吵闹,令我感觉负担过重。大多数社交活动,例如抢座位游戏等,都涉及唱歌。每天放学,他们把我送到地板光亮的大厅里,我母亲在那里接我。有一天下午,我正以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朝她奔过去,突然我停了下来,继
续表现出乎常的那种冷漠态度和退缩行为。我跟我母亲身体一旦紧密接触,孤独症的表现又回来了。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我能够表达明确的情感,但是,一旦密切接触,由于感觉方面的问题,我立即又封闭起来了。我一直盼望放学后有人来接我,但是由于患有孤独症,我无
法表达出来。与任何他人的身体接触都会引起刺激过度,这包括我母亲在内。孤独症患者不懂得尊重别人,因为我同每一个人的交往都经历感觉方面的负担过重。我年龄越小,越敏感,行为越退缩。我完全把自己同人们隔绝开来,为的是避免任何的感觉方面的负担过重。
折磨
我在——勒福医疗中心的最后一周,像是一场活生生的噩梦,因为医生给我做血液检验的时间最长。由于我待在——勒福医疗中心的日子即将结束,他们想从我身上抽取尽可能多的血液,只要不抽干了就行。
如同通常那样,我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忽然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摇摇摆摆走进门来把我带走。我被带进一个狭长的、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灰色金属制作的、标有刻度的医疗设备。—个护士用橡皮管把我的胳膊绑紧以增加血压,为的是更多、更快地抽
取我的血液。她用酒精擦了擦我胳膊上要扎进针管的地方,我紧张极了。
当他们拿着一根看上去大约有12英寸长的大注射器来到我的身边,我非常害怕。针管也比平时粗得多,因为要是使用他们平常使用的那种较细的针管来抽血的话,要抽满这么大的注射器恐怕得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在把粗针管刺进我的胳膊时,他们试图安慰我。但那护
土没能让我相信:一旦针管插进我的血管就会万事大吉。
当他们像一只巨大的蚊子在抽取我血液的时候,我哭了。唯一让我感到放松的,是我把目光盯在了灰色的度量设备上。我感到我仿佛在受到折磨,而且不移动针管就移动不了我的胳膊。我不断地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完事?真是痛煞我了。然而折磨在继续,直到他们抽取了足有—品特的血为止。
多年之后,我搞明白了,——勒福医疗中心一直把我当作一只供实验用的小白鼠来使用。还有什么其它理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抽取我那么多的血吗?原来我被牵涉到一项科研计划,血液检验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准是一直在做血液检验,以确定孤独症是由遗传决定
的,还是由环境决定的?
第二章 在儿童村
我在布鲁克林高地地区家里度过我的七岁生日。那是一个暖融融的春天,树上长满了新叶,看上去一片耀眼的嫩绿。五层楼上我们那安静的公寓沐浴着阳光,褐色楼房处在参天大树包围之中,鸟儿在歌唱,一派宁静的气氛。
我们住在希克斯街边上,距皮蓬公园只有一个街区。我们在依斯特河边上的游戏场正对着曼哈顿和有着自由女神像的纽约港。从滨海大道人们可以看到曼哈顿市区宏伟的全景,世贸大厦隐现在其他摩天大楼之上,还有那布鲁克林大桥。
那一天似乎充满诗情画意,起居室沐浴着缕缕阳光,我沉浸在温暖而宁静的气氛中。不过那气氛却被恐惧所破坏,我心中充满着再次离家的恐惧。我觉得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我试图享受在宁静的家里所剩下的这分分秒秒的时间。
不久,这种宁静就到了头,我父母邀请来和我—起过生日的一群孩子涌了进来,这是—批吵吵闹闹的家伙。这下子,我被噪声的声浪和充斥我感官的活动场面所席卷。至少来了十个孩子,他们的父母开车送他们来,匆匆忙忙进进出出,乱哄哄的,突如其来。我还没来得
及处理好这些吵闹声和感觉方面的负担过重,我就被安排坐在了餐桌前面的主宾席上。
为了隔开这些吵闹声和过分的活动,我全神贯注于视觉上的刺激物,例如带有金、黄、绿、门、黑色条纹的华丽墙纸,从顶而下,条纹的两侧是微型的几何图形和精美的花卉图形。在我注视着墙纸的日寸候,那些我父母认为是我朋友的小孩们坐到了我的周围,兴高采烈
地继续吵吵闹闹。我却被那些错综复杂的彩色图形所吸引住了,它们带我远离了吵闹的现实世界。
为什么聚会总是那么吵闹?为什么其他人对那种吵闹声不感到心烦?我无法和他们以任何形式交往。从另—方面说,那么多的人来庆祝我的生日,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是能单独和父母在一起平平静静地庆祝,我倒是会很高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日要
牵涉到那么多的外人,为什么不是我白己一个人来庆祝?这不是“我的”生日吗?
我知道我父母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听力有多么敏感。他们做了他们以为我想要做的事,他们做了正常情况下该做的事。由于我无法与父母沟通,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在一大帮孩子包围下有那么多的麻烦?我从未能设法去告诉他们,吵吵闹闹令我心烦,因为我以为所有其他人都像我一样听到了,然而我却从未听到过“他们”抱怨。
当大家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时,妈咪端出来一只漂亮的蛋糕,蛋糕上的蜡烛都已点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不愿意再次离家!但愿大家都安静下来!我甚至不愿意吹蜡烛,因为我不喜欢空气从我胸腔里呼出来的声音。在我们吃蛋糕和冰淇淋时,喧闹声仍在无情地继续着。吃东西是我能摆脱这聚会的—大赏心乐事,所以我就吃!我还喜欢打开我所有的礼物,就这样,这一天很快过去了。接下来,没等我明白过来,就到了第二天,我就上路去儿童村了。
我们带着包裹,跳上汽车。汽车开了,显然是去某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跨过臭名昭著的布鲁克林大桥,进入曼哈顿,这也是通向——勒福医疗中心和纪念医院的同一条路。过桥时,我心里闪过许多回忆,我们到曼哈顿去从来没有好事,总是去医院,而现在我又要到儿童村去了。
我们费劲地穿越东来西去的车辆向北驶去,到达第—大道和约克大道之间的东88街。总算周边地区还是安安静静的。
我们从绿色大众甲壳虫轿车里出来,朝着一栋有着新古典上义外观的旧楼走过去。在楼的巨大入口处,东西两边都有楼梯。我们扶着
装饰派艺术风格的、笨重的金属扶手往上爬,进入另一道门是宽敞的大厅,荧光灯把大厅照得灯火通明。我觉得就像在旅店登记似的。大
厅里放着闪闪发光的塑料椅子,相邻的是会议室和办公室。我们在光亮的、反射出荧光灯光的大理石地面走过去,这足以使人头痛眼胀。相邻房间里的地毯和装饰都很时尚,都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样式,闪光的塑料家具在荧光灯下泛着棕色和桔黄色。我们在大厅里等待我的陪
同人员把我领到楼上,今后我将在那里生活了。
我被弄糊涂了。我不知道怎样去告诉母亲,我不愿意单独留在那里。然而,因为我以为儿童村是我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我想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们都不会让我回家去了。太晚了。决定已经做出了。我很害怕。我不想留在那里,不想和不熟悉的环境、和不认识的
人在一起。但我从来都没想到要说些什么,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命运。就像我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我姐姐死了,我父亲离家出走了,我被送到了——勒福医疗中心,等等、等等。
我这一生都中别人替我做出决定,无论人们判决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其他的道路是无法想象的,对这种可能性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我从来不知道即将来临的事,我唯—需要做的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瞧,这下子又到了儿童村。
我们在楼上放下东西,再下到大厅里,我母亲紧紧地拥抱了我以后才离去。看到母亲离去,我真是太难过了,这下子我一个人留在了那里,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我无法表达我的情感,我完全被新的环境弄得不知所措。由于我不能传达我内心的情感,我母亲不知道我内心
惶恐到了什么程度,孤独症妨碍了我用词语来表达情感。我就是说不出自己的感受。在拥抱和亲吻我、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母亲难过极了。我没看出来,她并不想让我离开家,而我也不想离开家,但我就是找不到要表达的词语。
我母亲为什么送我到这里来?当然,她不知道我的感受,因为我是如此冷漠,又不能表达内心的感情。我仍然不能把词语和情感联系在—起,找不到能传达我的感受的任何途径。
每当我母亲有什么事问我的时候,通常,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一个“是”或者“不是”。这世界、我周围的—切都困扰着我,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去感受、去表达情感。我母亲和我第一次去儿童村时,她还没有决定是否要送我去那里,她曾问过我是否真的愿意去?她给了我机会来说“不”,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犹犹豫豫同意了,心里想她是愿意我去那里的,而我愿意她高兴。我希望一旦到了该我离家去那里时,一切都会顺利的。我所能做的,只是设法去适应离开家以后的生活,而不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
在第一次访问了儿童村之后,我们回到家里,几乎没做什么讨论。过后,我把这—件事忘了,因为我比较喜欢那里的氛围,不喜欢——勒福医疗中心的氛围。那里不像医院那样没有生气,与其说是医疗设施,不如说是一个住处。直到我真的要离家的前几天,我不得不去那里的现实,还并没有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打击。
现在我得待在儿童村了。现实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但是—切都太晚了,不可能再回去了。母亲刚离去,他们就领我进入了狭小拥挤的电梯,上到三楼我要生活的地方。我们刚刚从电梯里出来,我就遭到孩子们吵闹声的猛烈袭击,这些孩子看上去都像是正常孩子。气氛出
入意外的温暖,不过那地方很散乱。
起居室很大,有电视、长沙发和小沙发,那些小沙发看起来坐进去一定很舒服。旁边桌子上亮着白炽灯,作为对自然光的补充。这带来一种温暖的气氛,不过什么也比不上家的温暖。房间中间方柱子边上放着一张白色的大而圆的桌子,起居室是供游戏和看电视用的。
用餐的地方给人更多的是身处公共机构的感觉,氛围一点也不轻松。不久我就发现,它像一所小型学校里配有食物的自助餐厅。食堂里的所有桌子都足光亮的白色塑胶桌面,基座是不锈钢的。桌子配有桔黄色的、看上去很结实的椅子,都是金属制成的。餐厅的家具外观
都很实用,地上铺着深棕色的地毯。餐厅隔边的小厨房配有橄榄绿色的厨房用具。整个餐厅都在颂扬20世纪七十年代的那种炫耀的色彩,带着浓重的黄色、桔黄色、棕色和橄榄绿色。
这对我的视觉来说,是非常刺激的,有许多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东西。过道、起居室和餐厅的大部分墙面上,距地面三英尺的地方都装有黄色、桔黄色和棕色的仿木嵌板,嵌板以上的墙面都刷成白色。起居室和过道上的地毯颜色是与之匹配的浅棕色,带有红色和蓝色的斑点。
我被领到楼层的后部,那儿有两个大卧室,每一个卧室里配有三只床,还有一间大洗澡间,供起居用的区域备有大沙发,还有通向壁橱的过道。这部分带有被隐藏起来的微妙感觉。
起居用区域对着通向壁橱的过道,壁橱是供存放贵重用品之用的。壁橱本身朝向窗户,从窗户往外可以看到后花园,那里有许多树木,其他大楼后面都有院子,非常像我曾为之入迷过的那—种。至少,这里很安静,远离大街上的各种噪声。
我的房间要比起居和用餐的区域漂亮,因为内部的布置色彩柔和,它面对的不是大街,而是一片树荫。家具是棕色仿木纹的金属制的、带有青绿色的装饰;床上用品蓝色的,尽管墙是白色的、地毯是绿色的,但整个房间有一种蓝色的感觉。窗上装有风扇,但没打开。一张典型的宿舍用办公桌,上面有青绿色的金属搁板。我的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两个人,看上去和大学宿舍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我觉得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像海绵吸水一样把我的新环境,新的色彩和新的氛围牢记在心。我仍然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色彩上,完全不去接触工作人员以及十多个住在同一楼层的女孩子。耸立在我卧室窗外的挺拔的橡树似乎比那楼还高大。我往下望去,审视那些院子以及附近人家的花园,审视那些来去随意的人们。
已经是五月下旬了,我能听见栖息在城市丛林中的鸟儿在吱吱地歌唱。树叶又绿又厚,像雨林一样,仿佛从城市里搬了出来。因为我的房间往外能看到植物园,我不再觉得我还生活在纽约。这儿出人意外的平静,非常宁静。
起初,我睡觉的床像活动桥—样,是从墙里拉出来的。由于我是新来的,我有一个高大的、仿木纹金属和塑料制造的移动式橱柜,看上去就像楼里其他东西一样没有品味。过了不久,我就会升级到正常的床上去,但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这移动式橱柜所吸引。从
各方面看这真像大学宿舍的房间。
我同房间的一个女孩叫阿列克茜斯,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她的年龄和我相仿,娇小玲珑、性格开朗。又长又密的波状头发,梳了一个马尾巴发型,与之相称的是她深棕色的眼睛和褐色的肤色。她有一张漂亮的园脸,总是挂着微笑。我在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因为她看上去非常泰然自若,很高兴有了新的室友。
和我同房间的第二个女孩是康妮,她与阿列克茜斯不一样,是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她个子一般,骨架很大,长得丰满迷人。她那和肩膀一齐的头发卷曲浓密,更增加了她的富态。她是犹太人,带着浓重的纽约口音,这使她看上去比较敢作敢为。她总是前后挥舞着她的胳
膊,嘴唇皱缩起来像个球茎,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势。她也爱说话,除了挥舞胳膊以外,似乎也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她大约九到十岁,身材宽大。她的个性直率、吵吵闹闹,也调皮有趣。
沮丧与想家
在我与同屋的女孩见了面、在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我再一次想到,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回不了家。我开始感到非常沮丧和想家。第一天我逛来逛去,不知道蚂咪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会来看我。我只想她开车来接我,领我回家,但是没门。我觉得自己成
了孤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母亲。
我信步走进了餐厅,从两扇窗望出去,我能看到—个普通砖墙砌的、空无一物的小回廊。墙上的许多扇窗户都从外面涂上了油漆,不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东西。回廊黑沉沉的,毫无生气,望到底是沥青铺的地面。砖墙上面烟熏火燎,其它的一切看上去都是灰黑色的,像—个四边形的坑。
我—连好几个小时往下盯着看那回廊,不说—句话,一直在哭。有—个辅导员过来想安慰我,但我仍然—直盯着空无—物的砖洞。辅导员叫汤姆逊夫人,她非常有同情心。最后,我向她敞开了心扉,说我急切地想回家。她安慰我冰,我可以周末见到我的父母。但是她的安慰没起作用,因为我需要马上回家,而不是其他。汤姆逊夫人握住我的手,不停地设法让我高兴起来,但是什么也不能把我从沮丧和被遗弃的感觉的黑洞中拉上来。我感到离家十分遥远,我陷入了已经成为现实的噩梦之中。我没法醒来。
每天,我都会被吸引来到餐厅最远的角落里的同一扇窗户前,向外注视着那毫不引入注意的回廊。我喜欢那回廊:冷漠、空旷、黑暗和凄凉,它真的是我唯一的朋友。这种灰心丧气的待人态度持续了有几周时间,辅导员们只好让我—个人呆着去。他们准中以为,我是没
法帮助的,是—个没有希望的个案。我真的很失望,因为我感到我的情况根本没有出路,是我无法醒来的噩梦,我觉得被陷入了监狱之中。
几天过去了、几周又过去了,我仍然对着自己、对着我空虚的世界哭泣。有一天,正当我坐在那里盯着那个凹坑看的时候,我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Moody情况Blues演唱的《白色缎子般的夜晚》。我一边听着那首歌,两个眼睛却盯着回廊—扇窗户上—些正在剥落的漆皮。剥落的漆皮好像墨迹斑斑,看上去特别有趣。当我坐在那里被歌声和那墨迹样的东西所催眠的时候,我的情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触动。
我被无法估量的悲哀所激怒,凄惨地哭得昏天黑地。我被强烈的、冷漠的空虚感所压倒,开始喜欢那正在剥落的油漆。我恰恰像是正在被剥落下来的东西,没人理解我的痛苦。我觉得我并不比正在剥落的油漆更重要,因为没人要我。我陷入了沉丧的黑洞,无法控制哭泣。
听着《白色缎广般的夜晚》那首歌,真的加重哀我的悲袁和被遗弃的感觉,因为那是一首关于一些人拥有爱、而另一些人没有爱的歌。我感到我就是那个没有爱的人,他们唱的真的就是我。我被那音乐所吸引,一面不停地哭泣,—面盯着正在剥落的斑斑油漆,我完全被压垮了。—连几天,我都是这样的感觉,根本不想同他人交往。我的词汇表里没有“交朋友”、没有“与人交往”这些词汇,我只是善于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宋。我感到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放弃了我,我是—个迷失了的目标。
过了三个星期,我才被允许去看我的母亲。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仿佛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民。尽管我最终能够和她在一起了,我松了一口气,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我必须等待这么长的时间。我不能表达任何的情感。我母亲曾回忆说,我像“—个木头的印地安人”,甚至没有拥抱她。这一次见面很快就结束了,我没说什么话。我仍然不能和她建立感情上的联系,而且被遗弃的感觉太深了。
在三周之后首次见面期间,我们去了游戏场。这是六月风和日丽的—天。我现在还已得,我们走进—家商店,我要我的母亲给我买—本着色技巧的书,她给我买了一本。但当我要她买别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她说:“不行,我不能惯坏了你。”在儿童村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才见到她,我根本没有被惯坏了的感觉,而是感到从来没有这么讨人嫌。我想,她要是真的爱我,她至少要给我买点什么别的东西,以补偿我所经历过的这—切。沟通的路线没有接通。
我哪里知道,儿童村当局不允许我妈不到三周就来看望我!同时,在我印象中,她不喜欢看见我,因为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才来。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她不能来看望我,所以我总是往最坏处去想她。我丝毫不知道她是那么急切地要见到我,丝毫也不知道是儿童村不让她这么做。他们不让我母亲来看我的理由是,我需要三周的时间来调整,而且提前让我去见我的父母,对我来说会是有害的。当局因为我的不正常行为而指责我的母亲,因此不让她来见我,以便把事情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他们迫使我们等待了长长的三周时间,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没见到我母亲的最长的时间。因为从来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件事确实让我很伤心。
我仍然非常退缩,我从未想到过要去告诉她我的感受,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家。我只是要好好表现,以便有朝一日能回家。我以为,我呆在那儿,是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我得接受这种惩罚,是因为我出了什么毛病。我真的认为,在某个方面,我的父母对我不满意。我真
的认为,要是在我们见面时,我真的能表现好的话,他们会让我回家的。
没人告诉过我,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儿童村去,所以我完全基于恐惧和误解得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我母亲不知道我的感受,因为她似乎并没有我的那种感受。看起来,我离开她那么久而没有她的消息,一点也没有让她感到烦恼。我的父母也从没说过他们的感受。我真的
认为,要是妈咪要我回去,她会马上带我离开儿童村。但是每次见面之后,她总是把我送了回去。因而我以为她并不想让我呆在家里。我做出的假设是基于我对母亲行动的解释,我感到每次我们见面的结果是我又回到了监狱。我的结论是:我没有用,我的父母有足够的理由
不要我回家。没人告诉过我,我得的是孤独症。我只知道我有些不对劲,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
通常,每当我母亲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而感到苦恼的时候,我非常不安,担心这会成为她把我送出家去的进一步的理由。每当我在一人独处、而母亲却要我下楼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我害怕我—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要不她怎么会这样大声喊我呢!
我没办法把我的感受说给我的父母听,所以在每周末短暂的探视过程中,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沟通。我母亲不与我沟通,是因为她认为,我太退缩在孤独症之中了,我没有正常的感情,或者说我不会理解她。而我不与我的母亲沟通,是由于我以为,她的感受同我的不
一样。我以为,要是有让她说话的任何理由,她都会说的。由于我们没有沟通,所以我们俩彼此都有误解。
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几周之后,我开始习惯了儿童村的生活。我再也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搁在心上,我要快乐起来。我不能够再忍受这样悲惨的生活,我得干点儿什么来摆脱沮丧的心情。因此,我开始与同住一个楼层的一些孩子交上了朋友,这在我—生之中,还是第一次。我的第一个朋友
是与我同住—个房间的阿列克茜斯,她是我曾拥有过的第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创造了交往的历史。有了社交生活,脑子就不会去想别的东西,日子也打发得快些。有阿列克茜斯做伴,我感到很舒服,因为她非常安静、温柔。她是—个胆小怕羞的女孩,有着每天晚上祷告的习
惯。我躺在床上听她小声祈祷,我什么都能听见。她总是跪下来热忱地祷告好长一会儿时间,我能够断定,她对上帝有着强烈的信仰,这真的使我被她所深深吸引。她很可能以为我听不见她的祷告,但我的听力过度敏锐,即使她的声音再小,我也能听见。我问了她一些祷告
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别的同龄孩子交谈。
我和阿列克茜斯相互认识以后,我们开始一起玩妖怪游戏,这游戏是某—天夜里我介绍给她的。我从自己生动的想象出发,发明了这些游戏,这些也是我最喜欢的游戏。阿列克茜斯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她不是那种在黑夜里就会害怕的女孩,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游戏。
我们喜欢有那么—点害怕,喜欢脑子里有来自地下世界的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