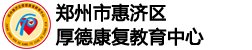为自闭症患者打开机遇之门
轰隆!踩到了自闭症“炸弹”。霎时间,爆炸的弹片击中了周围的每一个人,孩子、家庭、亲友、学校甚至社区。所有期望和梦想一瞬间都灰飞烟灭。
这就是曾在我18个月大的时候发生过的事情,自闭症让我丧失了功能性的语言沟通、发脾气、逃避周围的环境并伴随自虐行为。在自闭症还几乎不为人知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被诊断为严重自闭症倾向、发展异常和儿童期精神障碍。詹姆斯·杰克逊普特南儿童中心做出的结论是我可能不得不在福利机构中渡过余生 -- 即使幸运,也只能到庇护工场工作。我的父母誓言不让这种情况发生。
的确,我曾经在两家“机构”中呆过 - 不过不是福利机构,而是教育机构。一所是波士顿大学,在那里我获得了特殊教育博士的学位,另一所我目前还呆着“机构”是艾德菲大学,这里也是我致力于如何能够提高自闭症人士生活的地方。
即使处在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我的父母为了我也从未轻言放弃。虽然诊断的结果对我的父母是毁灭性的,但是他们却迅速地替我安排了类似现在的以家庭为主的密集式早期干预,内容包括音乐、运动、感觉统合和模仿等等。
从今天看来,我父母当时采用的干预方法更像现在的关系干预方法,比如米勒方法和格林斯潘的地板时光,而非行为干预和药物治疗。纯粹是出于为人父母的本能,他们给了我我需要的一切,而不是强迫我改变和融入。也许我父母的做法跟自闭症综合干预体系SCERTS模式最为相似,因为他们是在充分了解我需求的基础上,从已知干预方法中选择那些能够给我提供最好支持的方法组合。
起初,我的父母也试图让我模仿他们 -- 但没有成功。我的父母没有紧盯着封闭的大门,强迫我模仿他们,而是打开机会的窗口来模仿我。自然而然地,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开始不断地取得进步。
到4岁的时候,我又开始恢复讲话了。与此同时,我在詹姆斯·杰克逊普特南儿童中心的诊断也升级为只是有神经质,而非精神病儿童。
虽然我的父母那时候并不会意识到,但他们的确深远地影响到我现在所从事的关于把自闭症儿童的不同干预方法与其个性化需求相匹配的研究课题。而把方法跟需要相匹配是未来应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用一把锋利的牛排刀,我可以很轻易地撬开一只手表的后盖,拧开连接手表电机的小螺栓,然后陶醉在充满微型齿轮和弹簧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手表电机的这个微观世界对我更有意思的事情了。我的父母也为我的这种能力感到好奇,他们很快给我提供了一套装卸工具 -- 条件是我必须把手表的所有零件再按原样装回去,并且仍然能够运转!
他们没有把我拆卸手表的爱好当成一种古怪的行为,而是把它用作鼓励良好行为强化物,他们支持我的爱好并且利用它成功地塑造了我的高中、大学和就业,我不仅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自行车机械师,我甚至还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维修商店!
使用兴趣爱好和优势能力作为指导自闭症人士从事有价值的就业是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来,自闭症的诊断被视为一种摧毁生命和打破希望的毁灭性炸弹。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一直都在寻找我能够做什么,而不是囿于自闭症怎样限制了我。他们是先行者,现在的社会正逐渐赶上这个概念。比如,在丹麦的Specialisterne组织创始人提出利用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症人士点的优势和能力在全世界为他们创造一百万个专业工作机会的目标。
发现和善用自闭症人士的优势能力,而非把他们的自闭症视为一种具有破坏威力的炸弹,将激发我们为他们打开机遇之门。
相关阅读: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儿童发育障碍中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自闭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的表现症状为以明显的社会交往障碍、言语发育障碍以及刻板的兴趣、奇特的行为方式为主要特征。迄今为止,自闭症(孤独症)查不出病因,无法预防,也没有理想的药物可以治疗,自闭症儿童治疗只能靠矫正训练。2-7岁是训练的最佳时期。攻克自闭症(孤独症),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从2008年起,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2日被确定为“世界自闭症意识日”,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孤独症)的认识和关注。
自闭症儿童康复(孤独症儿童康复)目前只能依靠去自闭症(孤独症)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只有通过不断进行干预训练,才能使自闭症儿童掌握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而且自闭症(孤独症)是伴随终身的,目前自闭症(孤独症)的原因并没有找到,所以暂时是无法完全治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