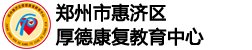中国雨人之谜 第五章 “孤独”的天才
更新时间:2004-08-30
点击数:
第五章 “孤独”的天才
孤独症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孤独症与白痴学者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雨人”是某些学者称为是“白痴学者”的另一说法,但被另一些学者认为是
孤独证的代名词。
英国孤独症研究协会会长洛娜·温在其《孤独症儿童》一书中这样谈及孤独症
儿童的特殊技能:
到目前为止我已谈到了孤独症儿童的残疾,但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
中间一些人具有某些特殊的技能,在这方面他们干得很出色。这给家长们一种感觉,
要是能找到这种难题的钥匙,他们的孩子们会完全正常的只要有某样东西能“使目
的达到”。一些人小时候就唱得很好,少数人能够演奏一些乐器,而且还有数量更
少一些的人还能够作曲。
这些儿童学会使用数学比使用词语容易。他们中间有些人能够以极高的速度,
在头脑中进行冗长的求各运算。他们往往喜欢机械性玩具,有些人早在学会说话之
前,就学会了操作收音机和录像机。
这些儿童之中有许多人在绘画方面有困难,因为他们在理解他们所见到的事物
方面有问题。他们画出看上去很奇特的图形来代表人类。另一些儿童更有进展,也
许绘图作画都很好,虽然他们差不多总是模仿他们看见的,或从过去记得的事物,
而没有创造性。
家长们往往注意到,要是这些孩子的特别收藏品被别人动过哪怕一点点,他们
也会立即知道。他们似乎能辨认每一块卵卵或者每一块木片,即使在成年人的眼睛
看来,这一件东西和另一件东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想像。这些孩子还可能找到只去
过一次的地方,而且知道在房子里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对他来说着着特殊兴趣的物品,
而这些房子他已经好几年没再去过了。
这些特殊技能没有任何一种依赖于语言。音乐、数字和地点记忆都是由大脑另
外的部分来处理的,不是与语言有关的那部分。有这样一些故事:孤独症儿童能长
诗或者很长的名单,不过是像鹦鹉一样学会的,而不能够正常流利地使用语言。
一般的规律是,孩子们在不需语言的技能方面成绩要好得多。
美国孤独症研究所所长伯纳德·芮慕兰博士文章中写道:“有一半的孤独症患
儿不说话,蓁的孩子则会不自然地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很多患孤独症的人拥有学者
型的心智能力,但这些技巧只是比较引人注意,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用。”
由此可见,“白痴学者”在孤独症儿童的存在是无须置疑的,虽然严格地讲,
孤独症儿童不能算作“白痴”。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工措词和概念上的束缚,
而去关注其实质的状态。
中国有3亿儿童,如果按每百万名儿童中有5名孤独症儿童的比例计算,则中国
有15万孤独症儿童,杨晓玲主任曾对我提到,每1万名孤独症儿童中约有1人是“白
痴学者”,则中国在理论上至少存在15名患有孤独症的“白痴学者”。我们有理由
相信,实际数目比要多得多。
我目 诸多白痴学者并不“孤独”,他们的社交能力很好,只是弱智。我们是
不是可以这样讲:孤独症儿童中有白痴学者,白痴学者却并非都是孤独症患者。
《中国妇女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光明
日报》、《女友》、《女士》……自1993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诸多的媒体上,都可
以看到田惠平的名字。她被记者们称作这样一个人: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兼而爱的
孩子,于是舍弃个人的生活,为千千万万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忘我而艰辛地工
作着。用一句古话,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当我采访这位38岁的弱小女子时,她却说:“记者们的报道有许多失误
之处,我被拔高了,其实我是一个很自私的女人,我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自私的目
的,都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的孩子。”
时下正在北京干得轰轰烈烈的田惠平是四川人,1987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德语
系,毕业后留校教语言,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教师。1985年,田惠平调到重庆建工学
院任教,同年11月,她生下儿子,1986年3月,田惠平休完产假从老家宜昌返回学继
续教书,学院给她分配了两居室,事业一帆风顺,生活幸福,应该说田惠平的生活
是美满的。
返校后10天,学通知有一个公派留学名额去德国留学,选中了田惠平。她把嗷
嗷待哺的孩子交给母亲,去了德国。两年后,当她又得以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时,她
发现儿子有些地方不对劲。在语言发育上显出迟滞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在与人相
处中表现出诸多障碍。她仅仅把这理解成孩子性格的特殊,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走进
医院的大门,听医生对她讲:“你的孩子得的是孤独症。”
田惠平真希望自己没有听到这句话!
田惠平带着儿子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诱,成都、重庆,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到
了。孤独症往往是陪伴终身的,田惠平被告知,治愈率几乎等于零。田惠平不甘心,
母爱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田。这个一向把事业看得很重的女人抛下了自己的工作,抛
下了正在起步的事业,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她寄希望于这座城市能够帮助她的儿
子。
杨晓玲教授认真地接待了田惠平。田惠平从她那里对孤独症有了更多的认为。
一位叫若梅的女记者这样田惠平到北京之后的心理和生活变化:
在她带着儿子来北京治病的日子里,她结识了一群同病相怜的侈位孤独儿的家
长自地地组织起联谊会,一位父亲这样谈到他的儿子:“他10岁了,从不迈出家门
一步,除了吃,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没有羞耻感。”这位父亲和妻子轮流上班,只
为了这个离不开人的孩子。另一位母亲说,自己的孩子进商店如入无人之境,信手
拿东西,她向商店的人解释说孩子有病,可哪有人相信她的话。
田惠平震惊了。面对40多位孩子几十位家长,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应运而生办
一个孤独儿康复中心。面对自己一个病孩子,无疑是个悲剧,而面向尽可能多的孤
独儿,将康复中心办起来就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田惠平开始走访精神科医生,翻阅大量的孤独症资料。据资料记载与专家介绍,
患孤独症的孩子实际上潜能相当大,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凡事不懂的现象,是因为人
们很难将信息送入他们的世界。这一切,给绝望中的田惠平开了一扇窗,她似乎看
到了儿子的希望,看到了众多孤独儿的希望。
田惠平放弃了她迷恋着的大学讲坛,放弃了合资企业那份收入颇丰的兼差,她
把自己的孩子安顿在四川老家,只身北上,开始四处奔走,筹办孤独儿康复中心。
为了获取专业知识与残联的支持,她走在精神病院和北京市残联之间。北京市教育
局、西城区幼儿师范、东城培智学校,凡可能对康复中心有帮助的单位,小田都跑
遍了。在一家幼儿园仅能提供的空间里,小田忙着布置,忙着招收新生,忙着安排
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一个康复中心终于在千辛万苦中搞起来了。
其实康复中心开办难,办起来更难。
没钱。市联残拨给的一点点开办费早告罄;尽管孩子的家长们每人出了800元赞
助费,依旧难以维持正常的支出。开学近一个月,矫正孤独儿应用的器具一件没有,
就连应准备的玩具都少得可怜。
没人。西城幼儿师范帮助解决了4名师资。然而,孤独儿难管,几乎是一对一的
管理,一天下来已将新老师边缘学科是精疲力尽;况且,孤独儿特殊的病态也令十
八九岁的小老师难以忍受。不到一周,4名老师走了一半。
辛苦。孤独儿永远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乱跑的,
吃牙膏喝广告色的,随意大小便的……田惠平带着两名老师以及两名自愿无偿服务
的家长,忙得团团转。
在田惠平的卧室兼办公室窄小的楼梯间里,来访者不小心都会碰了头,就是这
样的条件,田惠平依然亲自编写了教材,制订了每个孩子的培训计划。翻开培训计
划,开学才几天,那上面已记得满满的了。
我是在1995年11月29日采访田惠平的,这时她的康复中心已经搬过四次家了,
但是工作也纳入了正轨。
康复中心已经被国内外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一个幼儿
园都为田惠平的机构组织了义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赠送了16万元人民币经费,而
田惠平本人也获得了卫生部的奖励,1995年元旦还收到了享誉世界、拥有1亿读者的
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份证书,奖励她的“慈爱、勇气、尊贵,以及她的事迹对全
世界人民的激励。”
但是,田惠平却对我说,她当初之所以决定留在北京,开办这样一个“星星雨
教育研究所”,完全是因为想借此学会更多的救助孤独症儿童的办法,从而帮助自
己的孩子。她把儿子送回了四川,但是当工作刚刚纳入正轨之后,她便把孩子接了
回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正在北京一所启智小学读书。
田惠平说:“我真的很怎么呀!”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将如何评价这种“怎么”,我却只从中看到了一种真实的美
丽。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开始一项工作,这是很真实的人性的反应;而这项开始了的
工作却造福世人,它的福泽远远没有局限于自身,局限于一个孩子,而是成为千百
万孤独证儿童及他们家长的福音,更重要的是,成了一种榜样。我想这才是田惠平
的非凡之处。我们已经于从一种大公无私的角度来谈论一个人作的公益事业,仿佛
其中任何个人利益的考虑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有悖英雄人物形象的,其实,真实的
才是最美丽的,人性的才是最美丽的,虽然这份人性可能是怎么的。
田惠平告诉我,她出名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她,她真的不想出名!
她是一个年仅40岁的女人,远离丈夫,独自带着儿子在数千里外“闯世界”,
谁能够真正理解一个40岁的女人需要什么呢?
“我现在才知道,我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女人,我不要现在得到的这些东
西。我想要一个幸福温馨的家,一个安稳的生活。我想作家庭主妇,想整天守着丈
夫。我想做太太,想做平平常常的小女人,为把一日三餐做得精美些面耗费心机。
我甚至想生许多孩子,想时常对丈夫撒娇,想弄点小把戏逗丈夫高兴…只要有可能,
我真想随时离开这里,回去过家庭主妇的生活。”
田惠平对我说这些话时,眼睛亮亮的。我真的能够理解一个中年女人所需要的
这一切,我们都是平平常常的凡胎,普通人,谁不需要这些呢?但是,就在她对我
说这些的前几分钟,田惠平刚刚收到一份参加国际孤独症问题讨论会的通知,她兴
奋地跳了起来,说可以在那里讲一讲她的经验,讲一讲她的“星星雨”,甚至可以
得到一些帮助,使“星星雨”办得更好。
一个平凡的女人,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女人!
我总是无法被绝对伟大的东西打动,却时常感动于这种平凡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