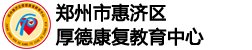中国雨人之谜 第三章 “天才”在中国露面
更新时间:2004-08-30
点击数:
第三章 “天才”在中国露面
中国精神科学领域接触“白痴学者”的历史可以推溯到1978年。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和中国人刚刚走出10年的阴霾,许多领域还都没有
理出个头绪,但历史却不再等待。
1978年初春的一天,一位母亲带着自己8岁的儿子,走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
生研究所,请示这里的儿科专家这位名字叫J的男孩的“问题”。
J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搞技术工作的。
“他可能是天才。”当母亲的说这话时眼里有一丝期待。
年轻的女医生杨晓玲接待了这位视视为“天才”的男孩,18年后,杨晓玲作为
这个研究所儿科的主任同我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
J的母亲滔滔不绝地讲孩子的情况,他刚上小学一年级,表现出许多和其他孩子
不同的地方。
J似乎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中,上谭时很难安静地坐在那里,而是左顾右盼。他生
活自理能力很差,不知饥饱,如果没人提醒他,他可能一天滴水不进,而只要不断
给他的饭碗里添饭,他就会不知饱饿地一直吃下去……他的交往能力极差,很难与
同学建立良好的交往,无法进行正常的交谈,凑在一起只是打闹,没有朋友。他对
事物的判断能力之低令人无法想象,与同学站在楼梯上吵架,同学在楼梯上,他在
下一层,上面同学向他吐口水,他也抬起头来向上吐口水,结果是口水都落在自己
的脸上,他也不知道躲避……
杨晓玲实在听不出有什么可以将J归入“天才”范畴的东西,在她看来,这是一
个典型的患有儿童孤独症的男孩。
“医生,这孩子不是病人,即使是,也是一个天才病人。”J的母亲坚持说。
“他的算术成绩特别好,而且会推算日期,准极了。”
“哦?”杨晓玲认真地听着。
“有一天,我和他爸爸闲聊,说哪天该发工资了。他在旁边听到了,立即插话
说:‘那天是星期四。’我们一看日历,果然是星期四,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自己
也说不出来。”J的母亲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我们便接着考他,看着日历问他某月
某日是星期几,他竟能对签如流。您说这奇不奇?”
果然很奇。杨晓玲问:“他平时常看日历吗?”
“从没见他看这。”年轻的母亲说。
杨晓玲拿出一张年历卡,现场测试。果然如J的母亲所说,杨晓玲报出一个日期,
J立即说出那个日子是星期几。
而相对应的,J的文字能力极差,不能简单的造句。
杨晓玲不能不感到困惑。
这实在应该归究于历史。就是在同一个时期,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关于白痴
学者的报道,但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医生,还无法接触到这些信息。闭塞,造成这
个国家在许多领域上的无知。
有一种“新鲜事物”刚刚被引进中国,那就是智商测验。人的智能高低竟是可
以通过一些问答测算出来,对于许多中国百姓来讲还是新鲜的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
当杨晓玲医生建议给J作智商测验时,J的母亲问:“能测出来是不是天才吗?”
可惜,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竟然还没有一套完备的测智商的设备!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著名学者、教授毛以雁先生被请了出来,亲自给这位“天才”
做智商测验。一流的专家在缺少一流设备的情况下测出了J的智商善:很一般,只是
在某些记忆能力方面比一般人略强。
医生们仍然无法作出某项诊断,这仍然不能责怪医生,而只能怪历史。
医生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建议家长注意发展J在计算和记忆方面的才能,既他的
算术成绩好,而且又长于记忆。
母亲带着他的儿子默默地离去了,不知道她对这个结果是否满意。
杨晓玲本能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很特殊的病例,J表现出的那些特殊才能的意义
虽然现在尚无法挖掘和验证,但终有一天会显出它们的学术价值。她记下了这位男
孩的家庭住址,这被时间证明是一个正确的举动。
智商测验并不尽善尽美的结果未影响J的父母将他们的儿子视为天才,当图书市
场上有了第一本关于速算的书时,他们立即给儿子买来,按着医生的建议,努力发
展儿子在记忆和计算领域的才能。收效的良好甚至超过了他们的预计,J对那本书中
传授的概念一点即透,迅速吸收,父母为他念了上句,他便不再需要听下句了。几
天后,J计算能力的提高便表现出来,父母用那本书上的题考他,他的回答速度远远
超过了书上认为“学有成效”的速度。
J再次表现出了让父母认为是“天才”的诸多特征。
事实证明,J的父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仅仅是因为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而是因
为J的确具有天才的成份,虽然这份天才在当时的中国尚无法被确认。
在J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两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杨晓玲医
生对他进行了一次家访,J在计算上表现出的超常能力引起了她的高度注意。
那时中国大陆市场已经有了那种可以拿在手掌上的小型计算器,杨晓玲拿着那
样的计算器对J进行了一系列难度越来越高的计算测验。
“5028-357?”
“4671。”
“12345+6789=?”
“19134。”
“12×30=?”
“360。”
“420÷60=?”
“7。”
“1209÷3=?”
“403。”
“1478×369=?”
“545382。”
“14789÷2563=?”
“5.7701911。”
“2589×2546=?”
“6591594。”
“258×357-6789+6541=?”
“98647。”
“98647×63-25891+234-568974=?”
“5620130。”
……
杨晓玲吃惊地注意到,每次当她报题目的话音刚落,J的答案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他仿佛不是在用头脑计算,也不是按着那些速算教材上指导的方法进行快速演算,
而完全是条件反射似的,似乎那些答案早已经在他头脑里了,而那多位数的复杂演
算题不过是提示他取出自己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某个物品而已。
“46890的开平方是多少?”
“789109的开立方是多少?”
……
杨晓玲提出更难的题目,J仍在她的题目刚说完时例立即说出了答案。而杨晓玲
手中的电子计算器还要比J的计算慢上半秒钟。
不要记忆了,J是一个年仅10岁,正读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
杨晓玲再一次见到J又过了三年,那是他的父亲领着来的。一种新的现象在J身
上出现了:时常兴奋地说些语伦次的话。J的父亲讲,这些话单独听起来不论在语法、
修辞还是意义上都没有问题,甚至不乏精辟之语,但是通过J的口连起来说时,便让
所有人听着都莫名其妙了。有时家里来的客人与J谈话,他便会突然间天南地北地乱
说一气,每句话都是完整的,但谁也搞不清他是什么意思,看不出来这些话与当时
有什么联系,更不知道J想说明些什么。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说明什么,也不想让他的
听众知道他的思想。
J的父亲问:“您说他这不是不天才的呓语?能破译吗?”那时中国关于飞碟的
报道正热,也许J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孩子像外星来客一样讲述着平常人无法理解,却
具有重大价值的某事事物。
杨晓玲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很可能J在看电视、听广播的时候,或其它场合听
到了些话,这些话人作为一些信号储存在他的头脑里。在特定的环境下,J启动这些
信号,顺嘴把它们说出来,那只是因为他当时想到了这些信号,而与周围的环境没
有什么联系,更与别人正在进行的谈话没有联系。J自己无法管理这些信号。
杨晓玲医生还得知,J因为实在跟不上正规小学的教学进程,勉强坚持着读到五
年级,不得不退了下来。他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能力太差,讲话死板,写
不了作文。这些都是孤独症儿童具有的障碍。
J一直跟姥姥在一起生活,这位老太太无意中又发现了外孙的另一个惊人的非凡
之处,他竟能对北京各条马路、每条胡同如数家珍,能够清楚地说出从一个地点到
另一个地点应该坐几路车,再换几路车,即使中间要换三四次车,他也能清晰地报
出来。而他只去过北京城很少的地方。杨晓玲对J这项新发现的功能做了测验,她随
便报出两个地点,J立即便清楚地告诉她应该怎么走,坐什么车。即使当杨晓玲选择
了最偏僻的胡同,J仍能立即反过来,仿佛他的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不,仿佛他自己
一张活地图,一部道路查询电脑。
J的姥姥承认,J的确整天拿着张北京地图痴痴地看,但他的这份兴趣只维持了
两三天的时间,随后便把地图丢到一边再也不理睬了。莫非,J真能够在短短的两三
天之内将那张地图吃透到此等吗?这其中的神奇奥妙只能问J了,但是J却无法回答
我们。
如果说J是一个白痴学者,那么他已经成为一个多方面的“学者”了。
对J的最后一次回访是在他21岁的时候,那时,包括杨晓玲在内的医生们对于孤
独症儿童、白痴学者都已经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而北医大的智商测验设备和水
平也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曾经在8岁时接受过智商测验的J在他21岁这年再次
被检验了智商,这次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73。73属于边缘水平。
J的智力障碍仍然一直存在,他的各种“特异功能”保持到21岁,同时,语言、
行为上的障碍也保持到了21岁。在生活上,他仍然无法自己关照自己,时刻离不开
别人。J仍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完全靠姥姥照顾。J的姥姥对医生讲了一些J的事情,
足以显现他的生活能力。比如说过马路,必须有别人领着,否则他肯定会被车撞到,
因为他无法衡量自己的运动速度和车速,并据此做出判断。而一些习惯的行为已经
变成刻板的了,比如从不使用家中以外的而所;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必喝两瓶汽水,
而这两瓶汽水必须从固定的某个摊点买来,如果这个摊点哪天没有汽水了,J则表现
得焦燥不安。
医生从表面观察J,他的眼神有些呆板,说话像背书一样,无法清楚地回答回话,
讲话的时候更无法进行适当的表情、手势的配合,不能写完整通顺的句子。
鉴于J的特殊情况,杨晓玲医生曾建议他的父母,是否可以让他学习、掌握一技
之长,以自立于社会。比如打字,也许适合J的智能特点。
那些回访是1991年,距离第一次见到J时隔13年,那以后,杨晓玲医生便再也没
有见过J。
采访已经成为北医大精神卫生研究所儿童科主任的杨晓玲医生时,我问她,不
是否可以认为J是中国医学界第一个有记载的白痴学者。杨主任想了想说,至少可以
认为J是中国精神科学术界最早有记载的接触过的白痴学者,至于其它领域,特别是
媒体上的报道,则很难加以统计了。
对于J的正式报道是1981年的一份学术报告中提到的,与他同时被写进这份报告
的还有另一位男孩子,但医生们不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提供某种治疗手段,而只能作
为一种研究的资料。
在那份报告中同时提供的是来自湖北省某市的一例个案。
1980年,一位母亲领着自己12岁儿子来到北京,她无法在当地为自己孩子的情
况“讨个廉洁”,将希望寄托在首都。最后,他们来到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
所,杨晓玲接待了他们。
这个男孩子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任何问题,长得很好看,眉清目秀的,只是当
人们注视他的眼睛时,能看出他目光中闪过的那一丝呆滞。与J的特点相同,他也是
能够熟练地推算日期,至于J有的其他才能,尚未在这个男孩子身上发现。他也在一
所正规小学读书,但无法跟上教学进度,自己对学习也没有兴趣。
男孩子的母亲告诉医生,她的儿子对日历表现得很珍爱,时时翻看,但并不见
得是在背。因为儿子的学习成绩下降,这位母亲便认为是对日历的溺爱使他“玩物
丧志”,一气之下,烧掉了儿子像宝贝一样藏在枕头底 那本日历,她没有想到的
是,唯一的结果是儿子为此精神失常了。他开始神志迷糊,整天对失去的日历念念
不忘,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吃不喝。
这位母亲后悔了,害怕了,带着孩子走遍了当地所有的医院的相应科室,最后
来到。
杨晓玲的手边正好有一本皇历,她当即对这个男孩子进行了测试。男孩子的推
算能力竟然可以上溯几十年,后推几十年,表现得比J还要超常。但是,杨晓玲仍然
无法解释,更无法“治疗”男孩子的问题。她只是告诉那位焦急的母亲,她的儿子
是儿童孤独症患者,医学上又称自闭症,只能对自闭症进行一些治疗,而不可能直
接治疗他对于日历的兴趣。
根据这两例个案写出的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重视。那以后,杨
晓玲又接触到了一些这样的白痴学者,特别是近一两年。
1994年,一个男孩子在母亲的陪同下出现在杨晓玲的面前,这又是一个孤独症
儿童,他的天才表现在对方块字非同寻常的记忆力,他只有4岁。
男孩子一出场,便引起了杨晓玲主任的注意。
男孩子刚走进杨主任的诊室,他的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对医生讲述症状,
他便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杨主任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向她的办公桌靠过去。他的母
亲拉着他:“这不是在家里,懂点规矩。”但男孩子是拉不住的,仿佛杨主任的办
公桌有某种魔力在招引着他,他向前凑着,靠着,挤着,眼中流露出一种饥渴。
“老实点!”那位母亲显然担心儿子的举动对医生太不礼貌,再次强行拉住他。
男孩子只稳定了几秒钟,又开始向杨的办公桌靠过去,这次更加饥渴和顽强,
眼神中已经流露出一种极度的痛苦,仿佛只有真正走近那张办公桌,他的痛苦才可
以减退。
母亲又在往回拉孩子,杨晓玲说:“没关系,不要管他。”
母亲带着歉意地说:“这孩子就是这样,不论到哪儿,只要见到有字的东西,
就一定要凑过去看个明白。”
男孩子终于如愿以偿地挤到杨晓玲的办公桌前了,他将头俯下去,杨晓玲这时
才明白,这个4岁孩子原来一直被她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纸工作计划吸引着。男
孩子终于看到那页纸上的文字了,他脸上的痛苦随即消失,露出幸福的微笑,显得
很美丽。他开始念那张纸上的文字,杨晓玲略有些吃惊地看到,他竟念得一字不差!
欲望满足了。男孩子的目光又开始顽固地落在杨晓玲案头打开的一本书上,那
是一本精神科的专业书,有许多专业术语,许多偏僻的字,杨晓玲把那本书递给他,
男孩子的眼里充满了感情,如饥似渴地开始翻看,然后竟通畅地念了出来!
对儿子天才能力的发现是从教他认字时开始的,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便开始教他
认字,令她大喜过望的是,儿子竟然过目不忘,那些特意买来识字卡片显的是那样
多余,这个男孩子只需要母亲指着一个字告诉他读音,他便可以记住,甚至不需要
母亲重复。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竟然记住了两千多个汉字。
男子子对汉字表现出极浓的兴趣,这种兴趣发展到他的父母无力招架的地步。
他把家里的每本书都一字一行翻看了,家长为他买来的新书,他总在当天读完,那
些儿童书无法满足他,他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任何有文字的东西。对于这些方块文字
的兴趣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一天不看到它们,他便坐卧不安。无论走到哪里,只
要看到汉字,他就要读出来。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立即就问,问过一遍之后再也
不会忘记。他就像是一台电脑,按一下键储存进去某项信息,只要是储存进去了,
就再也不会丢失。电脑还可以出现故障,但这个4岁男孩子的大脑却似乎永远不会有
失误。以这样一种状态去认识汉字,一年之后,这个男孩子所能达到的境界便是可
以想象的了,虽然这对于普通人是永远无法理解和企及的。
有一天,当男孩子的父母只想在客人面前显示一下儿子的识字能力时,他竟然
一字不差地为客人背出了一篇伊索寓言。那是一篇3000多字的寓言,当儿子开始背
诵时,父亲展开书给客人们看,客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目睹的事实,这个4岁的小生命
竟完整地记住了这3000多字,真的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仿佛是播放了一遍录
音那样准确无误。
再试另一则寓言,情况仍旧!
事后核证,男孩子的头脑里竟然完整地储存着13篇伊索寓言。是不是还有其它
数千字的文章被他一字不差地记在脑子里,尚无从得知。
杨晓玲对这个男孩子了一系列的测试,发现他可以准确地过目不忘地背出很长
的一段文字,但是,他却不明白这段文字说的是什么意思。
杨晓玲指着自己写字台玻璃板下的那张工作计划,问男孩子:“这是做什么用
的?”
男孩子愣愣地看着她,无法回答。
杨晓玲又指着“北京医科大学”几个字让男孩子念,这自然没有问题。杨晓玲
接着问:“这六个字连在一起说的是什么?”
男孩子仍直直地看着她,没有任何反应。
“它们说的是一所大学,你知道这所大学是和什么有关的吗?”杨晓玲进一步
提示。
男孩子仍不知所云,一言不发。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男孩子的机械记忆能力出奇的好,可以认识很多的字,背
下诸多的故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字和这些故事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仅仅是认识
那些字而已。他不理解,更不会使用。虽然他的脑子里有许多词汇,却同很多孤独
症儿童一样,无法自己用这些词汇来组成属于自己的语言。他可以完整地背出寓言
的原文,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这些故事。
像对待所有这类表现出白痴学者特征的孤独症儿童一样,杨晓玲对这个男孩子
的治疗仍然只能按着精神病症状来处理。
我是1995年11月30日采访杨晓玲主任的,这是一位十分热情、和蔼的女人,四
五十岁的样子。她提到,就在此时,还与北京市的另外两名白痴学者及他们的家长
保持着联系。
一位现年9岁的男孩子,是在5岁的时候来到北医大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他的天
才在于,一支曲子听过一遍之后就可以跟着哼唱。其对音乐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论
在哪里,只要听到音乐就不由自主地凑到声源处,全身心地谛听,然后跟着哼唱。
另一位也是9岁的男孩子,学校拒绝接收,因为他不听老师的指挥,不懂规矩,
无法与同学建立正常的交往。但同时,这个男孩子却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几笔之
间就可以勾画出一幅写实的钢笔画,有时还批上字。而他没有受过任何绘画方面的
训练。他与我采访的另一位提笔便作油画的完备我铮的不同之处在于,罗铮的画是
抽象的。
我提出想直接采访这两位少年和他们的家长,杨晓玲主任立即为我找出他们住
宅的电话,同时还提供了另两个可能在进行有关白痴学者研究的机构的名称。她的
帮助使我的线索立即增多了。
想一想18年前的1978年,当男孩子J第一次出现在北医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时,谁
会想到将近2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会有多位人士进行与些有关的研究呢?而对此领
域进行关注的作家,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
杨晓玲并非专门从事白痴的研究,她甚至否认自己在进行此项研究,她的专业
是研究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而这几例白痴学者不过是孤独症儿童中存在的特殊事例。
杨晓玲告诉我,大约1万名孤独症儿童中才可能发现1名白痴学者。
一家民办组织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在杨晓玲主任的努力下早已成立,
并正进行着艰难的工作。杨晓玲送给我这个协会编写的几期《孤独症儿童康复动态》,
以及协会集资出版的一位孤独症儿童的祖父翻译的《孤独症儿童家长及专业人员指
南》一书,此书作者则是英国孤独症协会主席洛娜温。在杨晓玲主任为这本书所写
的序言中,她呼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工作做出不遗余力的努
力。
孤独症儿童,虽然仅有万分之一可能成为白痴学者,但因为其总数的庞大,无
疑有充足的理由成为本书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