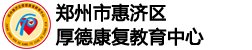我是孤独症人
当我两岁半的时候,开始表现出孤独症的倾向:不说话,重复的动作并发脾气。因为不能用词语与别人交流,感到沮丧的我时常尖叫。我总是被一种高频率的噪音干扰着,就像牙医用钻子在触痛神经。我长时间地摇摆身体或让沙子从手指缝流下,为的是逃避这种噪音的折磨。
孩童时期,我就像一个茫然无措的动物,总是在观察,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行为方式,但从来不会合群。当同学们疯狂地崇拜“披头士”的时候,我将他们的行为叫做一种“ISP”(interesting sociological phenomenon)——“有趣的社会现象”。我想加入到他们当中去,却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有少数几个朋友,他们有与我一样的爱好,如滑雪和骑马。但友谊总是在使我陷入一种违背自己的境地。
即使是在今天,人际关系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性”是最大、最主要的“罪恶制度”,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用的词。我从书本上和与人们的交谈中得出的结论是,孤独症人要么独身,要么和一个与自己有相同障碍特点的人结婚。
早期教育和语言训练将我从孤独症的封闭世界中拽出来。像许多孤独症人一样,我是用形象进行思维的。我的艺术能力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显露出来,并得到鼓励。我看色彩看得很准,能画出海滩上的水的颜色。
但是,词语对于我就像是外语,我需要先将它们翻译成彩色的影像,再配上声音,它们像录像带一般在我的脑子里过一遍。小时候,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用形象思维,直到我上大学后才明白,原来许多人是完全用语言思维、用词汇思考问题的。在我刚工作的时候,我以为另外一个工程师很笨,居然“看”不见他图纸上的错误。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的视觉思维能力较弱。
对于孤独症人来说,学习那些不能用形象进行思考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名词对孤独症孩子来说总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们直接地与某个形象联系在一起。直到我能够用视觉的形象将方位词固定在记忆中之前,它们(如“上面”、“下面”等)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在今天,我一听到“下面”这个词,我的脑海里就会自动闪现出一幅画面:防空警报响了,我自己钻在学校食堂的桌子下面——这是50年代初在美国东部地区常见的一种情况。
孤独症学生的老师需要了解他们的联想思维方式,但孤独症人的视觉形象思维比联想思维要多。各种概念都可以转换成视觉形象。小的时候,我弄不清楚“小的狗不是猫”,直到我观察了一大一小两个狗的鼻子,发现它们是相同的,我才理解了狗和猫的差别并不是在于大小,鼻子是辨别狗的通用标记。
我的职业与动物相关,而我的视觉形象思维能力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早期的一个畜栏设计项目是Arizona的一个畜牧养殖场里的一个消毒柜和牲畜入栏引道。消毒桶是一个窄长的、七英尺深的水池。小牛要独自穿过其中。桶中装满了农药,用来为牲畜除掉虱子之类的寄生虫。在1978年时,消毒桶的设计很糟糕,小牛们经常被弄得很烦躁,因为它们必须要经过一个陡而滑的斜道,所以它们会拒绝或跑掉。
我到现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置身于牛的大脑中,用它们的眼睛去观察。牛的视野很宽,因为它们的眼睛在脑袋的两边。在它们的眼中,走进消毒桶就如同从一个飞机的逃生道滑下大海中一样。所以我做的第一步是将滑道的斜坡材料由钢改为#p#分页标题#e#混凝土。试想我就是小牛的身体,有小牛的蹄子,我会很害怕走上一个滑溜溜的斜坡。最后的设计结果是一个混凝土的25度的斜道,道上有一条条的深槽,使牛蹄踏在上面会有安全感。斜坡逐渐地伸进消毒桶的水中,但牛看不见它将走进的水的深度,因为消毒液的化学成分使水的颜色变深。当牛浸入水中后,重心的下降会使牛平安地沉下去。
畜牧场的场主和管理者有时很难理解,如果滑道和消毒桶的设计合理,是可以让牛心甘情愿地走进去的。因为我是用图像思维的,我能体会和想象到牛的感受。今天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牛栏设备都是用的我设计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