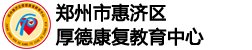触动天边星(上)
我第一次听说「自闭症」这个名词,应该有十几年了,后来也渐渐常听到或看到有关它的报导,多数是在杂志或报纸上看到相关的介绍,也曾看过类似题材的电影,只知道社会中存在着这种症状的人,但我对它的了解并不多,也未曾与此种症状的人相处过。
直到四五年前,我到六龟乡的一所体制外学校服务,第一学期班上就有一位小学二年级,典型的自闭症孩子,由于我在与这类孩子相处经验的缺乏,让我开学后的一两个月内,吃足了苦头。在无法有效互动之下,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一直深觉对不起他。
后来,透过学校同仁们持续的协助及研讨进修,才逐渐能跟他沟通互动,并了解他的思考及行为模式,也才有教学成效可言。可是当我们之间的默契逐渐加深,而他也慢慢地对我建立起信任感没多久,学期结束了,他父母也因搬家把他转到北部的学校去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周,每天放学,在等待他母亲来接他的时间,他反常地抱着我的大腿,直到他母亲来。之后几年,我就未曾再见过他,也未曾再与自闭症的孩子相处。
去年,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得以到星星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生态农场服务,我才再度面对自闭症孩子。每天我开着一辆八人座箱型车,载着会里的六个大孩子,从人车汹涌的高雄市火车站附近出发,逐渐开离市区,也逐渐远离人群,车子大约行使了五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位于田寮乡的生态农场。
农场的地形及地质,跟月世界差不多。贫瘠的土地,让农场栽种的蔬菜,显的又瘦又小。但是基金会却是不向命运低头,硬是要在这片不毛之地,进行有机农业的经营。就像基金会里的家长一样,要在这些先天有所不足的孩子身上,带他们学习生活的技能,以走出一条路来。
听说这些孩子自从在启智学校高职毕业之后,有人虽曾在庇护工厂及快餐店打工过,但是工作时有时无,有的则长期闲赋在家。尤其这几年,失业率上升,要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工商社会里谋得一职,真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基金会在远离市区的偏僻农场提供一个工作机会,让他们得以走出家门。
初到农场,虽然得带领几位自闭症大孩子进行工作及生活学习,但是由于以前在学校的经验,让我不再像四年前那般的不知所措。即使如此,农场的大孩子对我这样的陌生人,也呈现出典型的回避行为。
事实上,带他们操作农场里的工作,并不困难。他们总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甚少说话,只有阿智会作一些重复式的响应。比较有问题的是,他们对工作的持续性普遍不足。
阿楷是个体型高大肥胖的大孩子,憨厚率直,他可以自己每天搭火车到上车地点会合。在交通车上或在农场闲暇时,最常看到他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火车时刻表。他可以看上大半个钟头而不厌烦。
另外,听说阿寿刚来农场时,成天不讲一句话,见到陌生人,则躲得远远的。我刚到农场时,他也有着类似的行为。后来,才慢慢地会主动跟我讲话。可是,即使如此,在许多人面前,尤其陌生人,他多数情况下仍然沉默不语。同时,他也存在着严重信心不足的问题,有许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很容易做得到,但是他就是不敢尝试。有一次,一位负责炊事的黄老师请病假,阿寿跟我说他想念黄老师,想打电话给她。
我跟他说:「那你就打啊!」
阿寿说:「可是我不敢打!」
我问:「为什么?」
阿寿说:「因为我没有信心!」
后来我跟他说:「阿寿!你做得到!试试看!」经过约十分钟的鼓励后,阿寿总算自己打出那通慰问电话。
他挂断电话后,跑来跟我说:「我完成了!我自己打的!」然后跟我击掌庆贺。(这是我跟孩子的庆贺方式。)我注意到他先前的紧张不安,仍未放松,但他是兴奋的。
后来,阿寿自己打出第二通、第三通电话、爬楼梯上二楼关水、接听电话等等以前不敢尝试去做的事。每一次完成后,他都刻意地跑来找我,举起手,张开手掌说:「我自己完成了!」然后等着我跟他击掌!
现在他学会自己做、敢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话也越来越多,多到黄老师有一次说:「阿寿!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