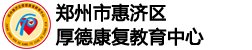英国“雨人”半世纪人生路
迈克尔·埃奇现年53岁,是英国最早确诊的孤独症患者之一。埃奇儿时,孤独症还是个新名词,患者往往被送进精神病院,受尽煎熬。埃奇有幸在父母和好心人关爱下长大,其成长经历为照料孤独症患者提供借鉴。
一个晴朗的日子,埃奇与81岁的母亲琼坐在家中花园里看照片。一张黑白照片颜色已经泛旧,上面还沾了茶渍。照片上,一家人站在一辆旅行拖车旁,其中女子30多岁,搂着两个男孩,面容姣好,却透着憔悴。埃奇用食指轻轻触摸她的面颊,说道“妈妈”,接着把食指移到戴着宽边软毡帽、腰板笔直的男子身上,说道“外公”。在另一张照片里,埃奇指着一名男子咧嘴笑道:“埃奇爸爸”。当看到一个穿蓝色套头毛衣的男孩时,埃奇认出那是小时候的他。
埃奇最初和别的孩子没什么不同,但到两岁半左右开始显露奇怪的症状。他的词汇量萎缩,直至不能说话,只能尖叫。他对母亲的声音没有反应,哪怕是呼唤他的名字也没用,但对隔壁邻居家孩子的声音、狗叫声以及其他声音极其敏感,而且会露出恐惧的神色。他对光亮着迷,喜欢围着灯不停转圈。家庭医生束手无策。
1962年,埃奇4岁时,父母带他去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看病。儿科专家肯尼思·索迪告诉埃奇的父母,埃奇得了孤独症。
此前一年,英国精神科医生、孤独症研究先驱米尔德丽德·克里克和杰拉尔德·奥戈尔发表学术文章,列出诊断孤独症的9点依据,包括“人际关系持续受损”、“意识不到个人身份”、“专注特定物体”、“竭力保持习惯”、“对声音异常敏感”等。
正是根据克里克和索迪这篇文章,埃奇被确诊为孤独症患者。先前,几乎所有英国医生把孤独症泛泛看作儿童精神病。
英国慈善机构“全国孤独症协会”说,英国现阶段大约每百人中有1人患孤独症,总计50多万人患这种疾病,而在1964年2月,“全国孤独症协会”前身“孤独症儿童学会”只统计到2000例孤独症。统计结果如此悬殊主要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孤独症知之甚少,不少孤独症患者没有被当做孤独症患者
医生开始认识到孤独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患者能够获得良好的照料。患者通常不到6岁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从此与世隔绝。
琼说,索迪医生确诊埃奇患孤独症后,就曾建议他们“把孩子送走,忘了孩子”,因为这种病好不了。她和丈夫克利夫抱着孩子离开医院,在附近公园里待了好久。琼看着儿子,眼泪止不住流,哭得眼睛都肿了。
夫妻俩没有听从医生建议把埃奇送进精神病院。“如果那时把迈克尔(·埃奇)送进精神病院,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知道那样的结果是什么——他会整天被灌药,”琼告诉英国《卫报》记者。
埃奇的父亲克利夫已经过世,生前曾是铁路维修工,经常上夜班,白天陪伴埃奇。“我下决心不退缩,”琼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挺过来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丈夫脾气不是特别好,但他对迈克尔(·埃奇)特别好。”
埃奇的外公厄尼不觉得外孙“有病”,特别宠爱他,每周日都去陪他玩,给他带糖果,放唱片给他听。
琼仍留着埃奇听过的唱片和已经坏了的留声机。“他过去(从康复中心)回家时就要放唱片,但是每天只放两张,那是他给自己定的习惯……除了圣诞节。圣诞节那天,他会想放多少张就放多少张,”琼说。埃奇眼下在“全国孤独症协会”在韦塞克斯开设的一家孤独症患者康复中心生活,定期回家看母亲。
埃奇6岁时,父母把他送到萨里郡贝尔蒙特医院开设的聋哑人学校寄宿,每周末去探望他,希望他能学会说话。他在那里学会一些词语。
埃奇10岁时进入肯特郡格雷夫森德一所新建孤独症儿童学校,在那里一直住到20岁。父母经常在他周末和节假日回家时带他去诺福克郡一个度假村玩,住小木屋。每次去玩,他都要去一家酒馆喝橙汁,吃油炸薯片,玩自动点唱机。
“他每次去都做同样的事。如果他想往西,我们绝不敢向东,”琼说。哥哥特里从不因为家中事事都要迁就弟弟而抱怨。
离开学校后,埃奇搬到他现在的住处。刚到那里时,他整天躲在屋子里,不愿出来,不肯与任何人交流。
工作人员曼迪·吉布森照料埃奇20多年。她说,埃奇的进步漫长而缓慢,但进步相当大。现在他有什么困难,会用言语表达,能做曾经对他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包括去公园游玩、去超市购物、游泳等等。
像不少孤独症患者一样,埃奇坚持一些习惯,从不改变。他爱吃鱼,正餐食谱总是鳕鱼配柠檬、薯片和豆子,加两袋番茄酱,吃完用两根吸管喝橙汁,然后吃太妃布丁配冰淇淋。
工作人员了解孤独症患者的特点,不试图让埃奇改变吃饭的习惯,但是天气暖和的时候,会鼓励他到室外用餐,比如坐在餐厅阳伞下,去公园,或坐在海边长凳上。
琼说,埃奇小时候不能说话,不会回答问题或者与人交谈,但“他能读出唱片封套上所有乐队名字……披头士、滚石。他酷爱音乐,我也是,我们总是在家里又唱又跳”。
埃奇玩拼图游戏可以不看图样完成拼图,甚至可以仅看拼图小块的背面把图拼出来。“他可以轻松做成这件事,”琼说,“但是如果拼图缺了一小块,我们的麻烦就来了。我们要手脚并用在地上使劲儿找,如果找不到,他会非常苦恼。”
迪安娜·赛比德是埃奇最喜欢的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之一。她说,人们对孤独症患者有误解,认为他们对人不感兴趣,不会与人交流,缺乏幽默感。
埃奇患病初期对父母说话不理不睬,却对母亲好朋友希尔达的嗓音着迷,能对希尔达的话做出回应。希尔达就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埃奇家陪伴他。
赛比德去年7月开始在康复中心工作,先前没有照料过成年孤独症患者,却与埃奇一见如故。“他一觉得紧张就会看我,看到我平静,他就恢复正常,”赛比德说。
埃奇会与赛比德开玩笑。一次,他把赛比德带到食堂一张餐桌旁,让她坐下,自己则端着盘子走到食堂另一头儿,一个赛比德必须扭转身体才能看见他的位置。赛比德一扭身做出偷看埃奇的表情,埃奇就看着她笑。“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赛比德说。
埃奇每周四晚上都与母亲通电话。虽然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聊天,但是他已经能说不少词语。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即每次说到最后,他说“再见”,母亲回答“再见”,这样来回说“再见”整整8次,他才会挂断电话。
在琼看来,孤独症孩子特别孩子气,但是很可爱。她说,埃奇给她带来很多麻烦,但也有很多满足,无论怎样,她都爱他。